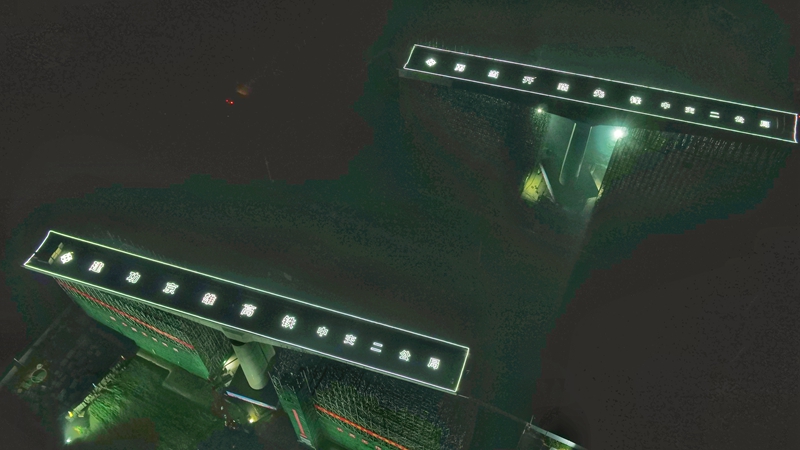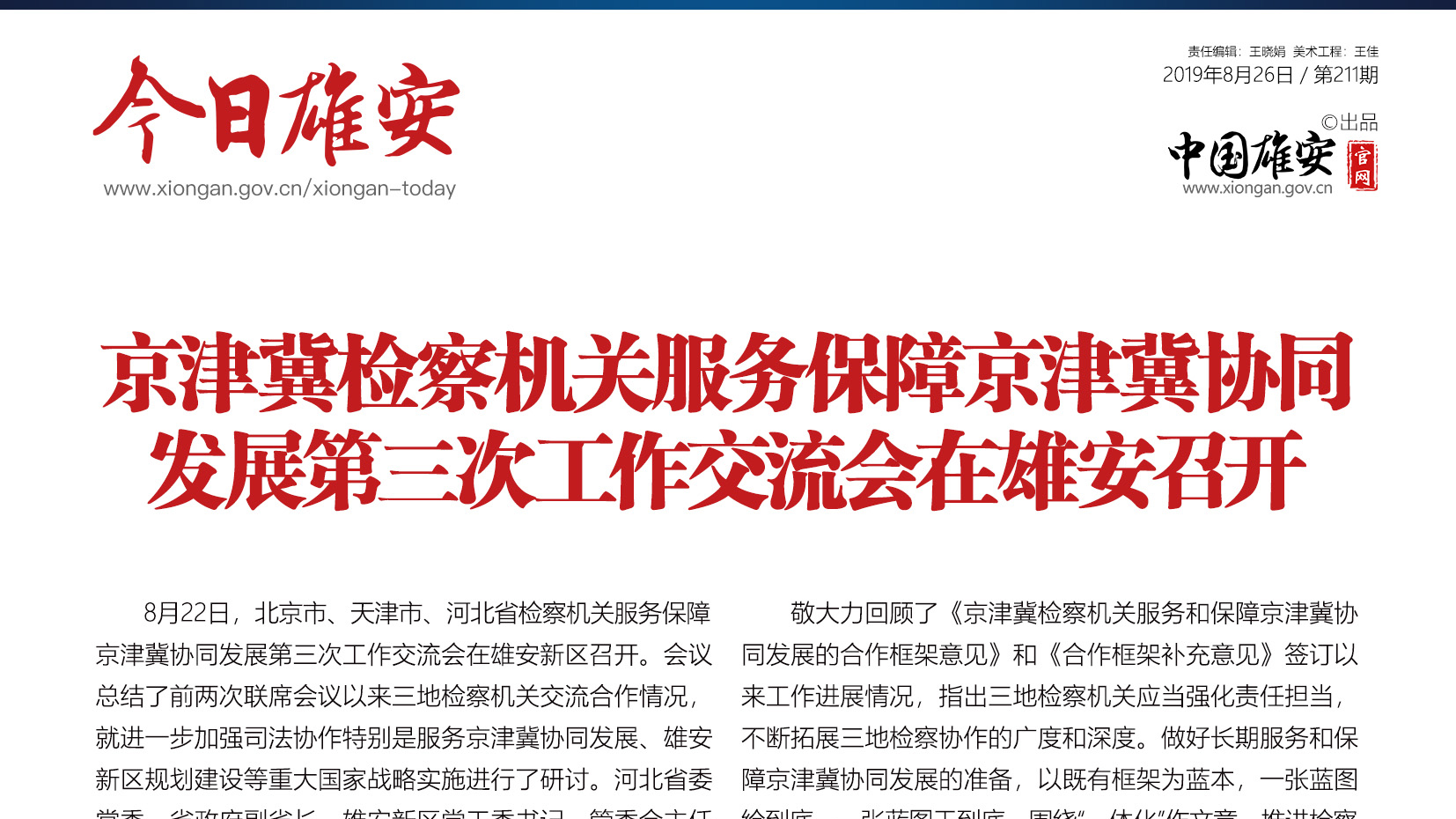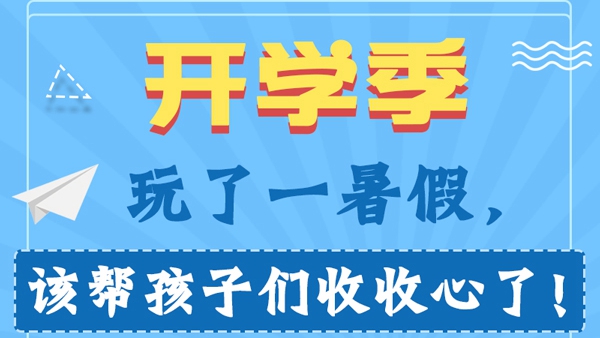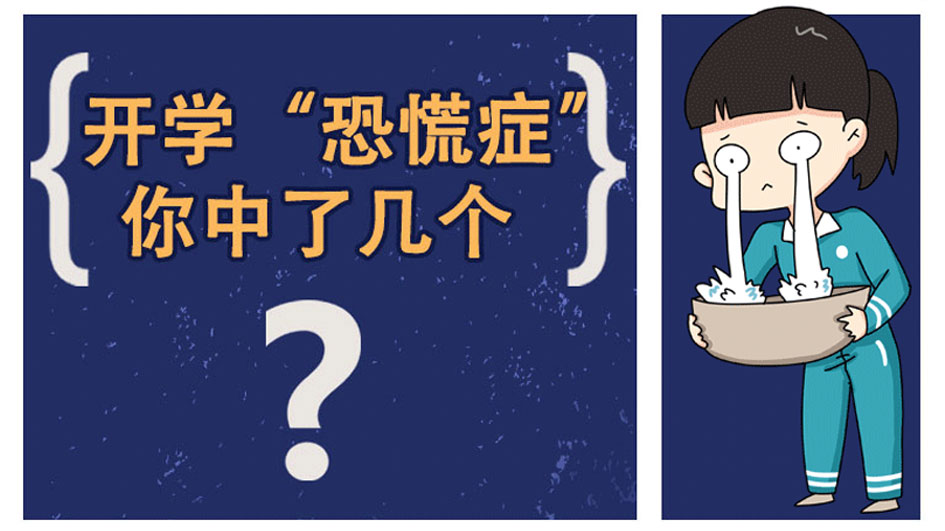鄭建黨
她是一位從雄安走出去的新聞媒體人,20年來,兢兢業業,恪守職責;她是一位從新聞行業跨界到作家群的媒體人,歷時四載,完成了一部長篇歷史小說《鐵肩錚骨楊繼盛》;她是一位奔波忙碌著的文化公司老總,正在為傳播雄安新區的優秀文化竭盡全力。她就是雄安新區容城籍資深媒體人鄭建黨女士。
記者:你是從雄安走出去的媒體人,請談談這些年來的感受?
鄭建黨:從走出校門那天起,我就一直在媒體工作。最初在容城縣電視臺做新聞采編和主持工作6年,后來到了河北電臺做廣告策劃和經營工作10多年,期間,還有一段短暫的省級報人的經歷。這幾年,我從體制內出來,運營公司繼續電臺工作,從節目制作到廣告經營,實現自己做“好聽的、純凈的、綠色的”電臺夢想。
回首20多年的媒體生涯,對我來說是個“意外”。我四歲才開口說話,六七歲時,說話還連不成句子,常常被人“譏笑”。因此,我從小喜歡安靜和獨處,善于觀察和思考。人們對廣電人的印象就是“說話”的工作。所以,我偶爾提到這段“無言”的童年經歷,很多人都覺得不可思議。當我拎著一堆業務證書和榮譽證書離開縣臺時家人不解,當我離開省臺自己做公司時有人詫異,當我跨界當作家時有人說我瘋了。我,只是喜歡自我挑戰。
記者:作為媒體人,你是如何創作出《鐵肩錚骨楊繼盛》一書的?
鄭建黨:我從小聽老人們說“容城三賢”:元代理學大師劉因(靜修先生),明代諫臣名士楊繼盛(椒山先生)和清初北學宗師孫奇逢(征君先生)。后來,我到容城縣電視臺工作,到縣志辦采訪時,從小縈繞在腦子里的“三賢”終于“真實地展現在我的面前”。恰恰是這次采訪,楊繼盛莫名地“揪”住了我的心。
1998年,我到了河北電臺工作。生存和生活的壓力,使我無暇思考當年那一“揪”究竟是什么?直到2014年,與我合作的電臺達到5家,可謂諸事纏身,社會的浮躁之氣也影響著我。有一天,我靜下來思考:人不應該只為了活著而活著,也不能只為了掙錢而忙碌,應該在有限的生命里,做一件有價值的事情。想到這兒,沉寂在心里多年的那一“揪”,突然在記憶中被檢索出來,且一發不可收。細品椒山先生殺身成仁的氣節又是一“震”,震撼的是我的靈魂。我不禁向生命大聲詰問:“這樣一位有俠義氣節的民族脊梁,緣何只沉寂在史冊?”一種強烈的念頭,促使我要做一次人生的極限挑戰。我到容城縣委宣傳部,與時任宣傳部長的劉彥坤和常務副部長王凱毛遂自薦說:“我要為楊繼盛立傳!”
由于當時我手頭史料較少,不僅要“接地氣”,還要寫出本土風物鄉俗。于是,我選擇了小說體裁,再發揮廣播人的優勢,錄成有聲書,實現大眾傳播。此前多年,我只為工作而寫,駕馭一部以先賢為主題的長篇歷史小說,其難度可想而知。但我堅信:凡事只怕用心。歷時4年,一部33萬字的長篇歷史小說《鐵肩錚骨楊繼盛》終于在2018年11月由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。此時距離1993年已過去25年,也是我離開容城整20年。
當時,有人曾勸我用網名“鄭四小姐”出版《鐵肩錚骨楊繼盛》,更能抓人眼球,但我認為本名更符合椒山先生浩然正氣的“氣質”。我相信:人如名,名如文。
記者:史學界把楊繼盛定義為著名諫臣或大明硬漢,請談談你理解的楊繼盛。
鄭建黨:楊繼盛因赫赫“兩疏”即《請罷馬市疏》和《請誅賊臣疏》,而丹心照萬古。他因第一疏被貶狄道(今甘肅省臨洮縣),一年后又獲“半歲四遷”的殊榮,上任京城兵部武選司員外郎。不久,他便以第二疏彈劾貪腐權相嚴嵩,還朝廷清正廉潔之風以報君恩。不料,奸佞當道,椒山先生入獄受酷刑后被扔進死牢,且斷醫斷藥。他用一個瓦片“自割腐肉,自斷腿筋”,憑借超強的意念活成了嚴嵩的噩夢。
這樣史無前例的驚天地泣鬼神的壯舉,說他是著名諫臣、大明硬漢,恰如其分。也正是椒山先生的浩然正氣,使他的生命太過短暫,似乎遮蔽了作為儒家士人博學多才的一面,以至于雍正年間進士、直隸博野縣人尹會一在編寫《續北學編》時,將楊椒山收錄北學大儒卻鮮有人知。椒山先生從小天賦異稟,留下大量詩詞。他在狄道辦超然書院、疏通河浚、整頓褐市、開發煤山,被百姓尊為關西夫子和楊父。可以說,楊椒山文韜武略,既有文臣的博學多藝,又有武將的俠肝義膽,是集俠義風骨、詩詞書法、音樂律呂、治世之才于一身的儒家士人。清初大儒孫奇逢在《楊忠愍公傳》中曰:“明代忠臣多矣,其忠烈震動天地者,公之外曾有幾人?……皆曰椒山可語進道矣,……豈不足為道學之宗哉?”
記者:《鐵肩錚骨楊繼盛》出版恰逢雄安新區設立一年多,從媒體人跨界作家。這其中你有何感慨?
鄭建黨:是啊,我決定為椒山先生立傳時,家鄉還是容城縣。書出版后,家鄉已經是舉世矚目的雄安新區了。有人說我“幸運”,有人說我“趕對點兒了”……我說:“任何一份初心和努力都不會被命運所辜負!”正如這幾年我運營電臺,前期無論多難,我都堅守“打造品牌電臺”的初心,得到廣播界的認可。而我寫書的初心,只是與先賢椒山先生“一面緣分”的一個交代,抑或還愿,是我生命中一件有意義有價值的事情。從媒體人“客串”作家,我還不太適應,曾自嘲地說,是“媒體人出門打了一次醬油”。然而,一年來因書而起的故事使我感嘆:書,只是“故事”的開始。
在我的書出版3個月后,一位容城人找到我求助說,“希望將父親留下的大量椒山先生遺稿面世!”他的父親是容城的文化名人楊秉誠,曾發表和保存有大量的椒山先生作品。我看后感到很震撼,經與容城三賢文化研究會會長王凱溝通,決定出一本紀念楊秉誠先生的“椒山特刊”。我牽頭把特刊作為容城文化界的一項公益善舉推出,先后有多位容城人做公益編委,特刊即將出刊。用椒山先生的話說:“人心莫高自由生成造化,事由天定何須苦用機關。”寓意我的《鐵肩錚骨楊繼盛》付梓可謂恰到好處。
記者:作為媒體人、作家與文化公司老總,你在未來雄安文化建設中有何期待?
鄭建黨:做媒體是我的主業。作家對我而言僅是一種機緣。正如《燕趙晚報》副總編輯杜世國說,鄭建黨是被“閃電”擊中的那個人,但不是每個人都如此幸運。我將“聽從內心的聲音,追尋先賢的羅盤。”未來的雄安將是一座高科技的智慧之城,在藝術文化領域將有更多的發展機遇,在融媒體時代,我將發揮媒體人的優勢,為家鄉的文化建設做好傳播和傳承工作。(記者 王淵)